吴 倩
(天津外国语大学 思政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影响力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天津 300204)
[摘要]台湾新士林哲学之集大成者罗光的儒学观在现代儒学研究中具有典型性和独特性。它以会通儒家与士林哲学为理论目标,在信仰源头上强调儒学与三代上天信仰之间的继承性,在形上基础上肯定儒家具有明确的形上学传统且与上帝信仰不相违背,在道德境界上主张由伦理的超越进至本体的超越。作为20世纪港台地区与现代新儒学并立的学术传统,罗光对儒学的现代阐释展现出迥异于新儒学的独特致思取向,堪称基于汉语基督教传统而重建儒学的典型范例。
[关键词]天;位格;形上学;人性论;境界
[中图分类号]B26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17)09-0045-05
台湾新士林哲学学派作为台湾岛内与现代新儒家、自由主义派鼎足而三的现代哲学派别,“研究成果和学术群体均颇具实力,且亦以中国文化为主要话题”,“是目前在台湾的一支影响较广、势力较大的哲学流派”[1]。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学派在大陆学界尚少为人知,因而对其开展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在一定意义上有助于拓展大陆学界的现代儒学研究。
罗光(1911—2004)是台湾新士林哲学的领军人物之一,堪称新士林哲学家中上承创始之端绪、下启大兴之盛势的中坚力量,也是其中真正完成了完整体系建构的第一人。他一生学思勤勉,著述等身,且以儒学为治学重点。罗光毕生致力于发掘士林哲学与儒学在学理上的相通之处,力图使两者相互诠释、相互补充,进而一方面使中国文化向基督信仰开放,另一方面从儒耶会通的视角思考儒学现代转化的可能方向。本文选取罗光全部学说中最为基础性的儒学观进行梳理、论析,以分析其思想洞见和理论启示。
在罗光看来,儒家哲学从总体上可以用“生命哲学”概括言之。罗光在《中国哲学思想史·先秦篇》中讲道:“生命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没有这个名字,在西洋哲学史里也只有现代才有这种哲学;但是在中国哲学思想里,生命的思想充满了儒家的哲学。‘从《易经》开始,“生生之谓易”把天地的变化都集中在生命一点,生命成了宇宙的中心。孔子以仁为自己的一贯之道,仁即是生生,即是爱惜生命;孔子的仁的哲学,便成了生命哲学。’”[2]258基于这种思考,他以“生命哲学”来阐发儒家思想的特质,这种以“生命哲学”为名的儒家哲学主要包含了信仰源头、形上基础和道德实践三个方面。
一、信仰源头与一贯之道——超越界的掘发与开显
罗光会通儒学与士林哲学的努力首先体现于对《诗》《书》中的“上天信仰”这一儒学源头的阐发。他在《中国哲学思想史·先秦篇》中指出,儒家思想在其源头上是一种非常成熟的宗教信仰,而其全部意蕴“只在一个‘天’字”,这个开启后世儒学一贯之道的上天信仰“在《书经》《诗经》中乃指着有位格的尊神上天或上帝”。[2]27
具体地说,这一“上天或上帝”是宇宙的最高主宰,其本性为无形无象、最高最大、具有位格的精神体,也即“人格神”。这个主宰之“天”造生人物,制定法则(自然法与人生之道),监临万有,赏善罚恶。这个独一无二的造物主“上天”不受物质形象的拘牵,超越于万有之上,为一切知识和价值之源。更重要的一点在于这一精神体具有位格,也就是说,造物主“上天”是一位单纯而完整的理性自立个体:一方面,“天”是一个单体,与其他个体不相混同,居于一切神灵和物体的最高级,从本体上说是完全独立的自有,不依赖任何他物而有。《诗》《书》里讲的便是作为最尊神灵的唯一的“天”,它创造并监临万物,绝对不与宇宙等他物相混同。另一方面,“天”有理性和意志。从《诗经》里的“明昭上帝,迄用康年”
(《周颂·臣工》)、“敬之敬之,天维显思……陟降厥士,日监在兹”(《周颂·敬之》)和《尚书》里的“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虞书·皋陶谟》)这几段话中可见:“上天”有理智,有无限的智慧;并且,“天”能显明其怒威,这表明“上天”有意志。因而,三代时期所信仰的“上天”不是盲目的自然神,而是具有位格的最高之人格神。
罗光在此着力强调“上天”为一最高之人格神,意在阐明:这个作为一切真善美的价值之源的“上天”不是一种超绝于人、让人难以沟通的超自然力量,不是一个无位格的、渺茫的实体,而是有心灵的、与人相似的神明,“至高至上,至美至善,有热诚的爱,有体贴人情的智慧”[3]352。罗光曾经多次指出,“上帝”的位格性特征表明,这一至高的造物主愿意而且有能力与那个有别又类似于自己的“他者”(人类)建立关系,以其至高的爱及于人类,进行启示和救赎,而不是一种遥不可及、无知无识的超越性。罗光于此所讲的超越性显然是依照其所熟悉的基督教传统而来,但也符合三代之《诗》《书》传统。我们可将之与现代新儒家所讲的超越性略作比较。新儒家的典型代表牟宗三指出,《诗》《书》中的“帝”“天”只是凸出了一种超越意识,一种“超越的亲和性”(引曳性 Transcendental affinity),“冥冥穆穆运之以前进,是这样意味的一个‘天’。并不向‘人格神’的方向走”。[4]这种超越性被后儒进一步阐明为“为物不贰”“生物不测”的“创生实体”,且可以避免作为人格神的“天”之于人的隔阂与疏离感。应当说,关于人格神与“创生实体”何者更为亲切的意见分歧实为信仰问题,难以衡断。本文于此想要说明的是,相对于新儒家以“天”为与人之德性相同一的“创生实体”、强调人之自足和自信的天论而言,罗光的主要特点在于从儒学发展源头上肯定一个“超越界”的存在,肯定天、人在根本上不可“同质同等”的异质性,凸显人之有限性和超越自我的必要性,进而通过“上天”这一代表超越界的人格神来与普通人建立关系,以助人由有限的人性超越至无限的、至高的神性。
通过对《诗》《书》中“帝”“天”信仰的着力阐发,罗光揭示出儒家思想在其源头处所蕴含的超越之维。与学界的早期儒学研究多以宗教信仰为负面的先民迷信而以儒学为脱胎于信仰的理性转向不同,罗光的阐释着力显发儒学对三代信仰之基本精神的继承,注重超越信仰之不离于儒学义理的必要性——这在下文形上学与道德论的分析中将进一步展现。同时,罗光也坦言,后世儒家学理系统中的“天”字大多并非代表宗教信仰的尊神,但是,历代儒家学者在其生活之中,却无不保有这种对于“上天”的信仰,如孔孟以“上天”交付的使命自任,社会生活中的帝王承“天命”而治民、祭祀,均是这一信仰的具体体现。因而,基于这种生活的儒学,并不排斥此一超越的人格神信仰。
二、儒家形上学——学问基础与信仰指向
在信仰源头之外,罗光进一步阐明了自己对儒家形上学的独特洞见。当时西方学界多谓儒学仅为研究人生问题的伦理学而不承认其具有形上学,针对这种观点,罗光撰写了《儒家形上学》一书,并在其他相关著作中多次强调,儒家哲学具有自己的形上学传统,儒学是在形上学基础上讲论伦理学。
应当说,罗光之所以得出上述论断,首先是因为他对形上学之内涵和研究对象的研判。他认为:“普通哲学研究宇宙、人、人的生活,分为:宇宙论、心理学、伦理学。在研究这些部分以后,追求最后的理,乃有本体论研究‘有’,以研究‘有’的哲学为形上学。”[5]可见,形上学就是对事物最高理由的研究,学术无论东方西方,均以此为基础,因而非唯西方哲学才有形上学传统。并且,若就其最根本的意义而言,中西方的形上学可以说并无二致,都是对最终之“有”的研究,差异只在于二者对“有”的研究进路不同。相对于西方形上学以静态分析的方式研究“有”(being)的意义、要素和原理,中国哲学乃以“有”为“生生之动”,从“动”的方面通过万有变化之道(“变易”的“在”)去研究。中国哲学以变易之“有”为本体,称之为“生命”;认为世间每一种存在都是一种“动”,“动”的本意则是“生”,中国形上学的性论正是对“生生之动”的研究。
通过这种分判,罗光得以贞定儒学的形上学传统。他进而指出,这一传统由《易经》《中庸》开端,主要实现于宋明儒学。儒家形上学始于《易经》“生生”之道,宋明时在孔孟人生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把《大学》《中庸》的思想与《易经》相通,进一步说明了人性的形上本体,形成了天道、人道两方面相结合的完整体系。如果按照现代学术的分类方法来对照宋明理学,罗光认为,理学家们在宇宙论方面讨论了太极和阴阳,在本体论方面讨论了理和气,在人性论方面讨论了性和理、心和情,这三方面集中体现了中国哲学对于物体本性或最高理由的独特观点,构成了儒家的形上学。对于这种独特的儒家形上学,罗光着力于阐明如下两点:
第一,整个儒家思想以形上学为基础和中心,人生之道乃是在形上基础上而有的伦理规范。在《儒家生命哲学》中,罗光指出,从儒学发展史的角度看,儒家是由讲论人生之道而追溯至天地之道,“天地为宇宙,在希腊哲学为研究的第一对象,在中国哲学为研究的第二对象”,然而,尽管宇宙观在发生的顺序上后于人生之道,但“在逻辑上说,则先该讲宇宙观”。[6]也就是说,儒学在义理逻辑上应当是从形上学进至伦理学,在形上的基础上讲道德伦理。这种判定鲜明地体现于罗光的多处儒学史诠释中,例如,《中国哲学思想史·先秦篇》里面对“仁”“诚”等主要范畴的诠释,均是以形上的本体义为重、为先,德性义乃是建基于“仁”“诚”之为生命的发展、实现之本体义的。对此,罗光曾经明确讲道:“中国哲学具有形上学,由形上学而到伦理学。中国形上学讲论万物的存在,以存在为生生。生生在各级物体逐渐表现,达到最完美的程度时,乃有高尚的伦理生活。”[7]也就是说,伦理学乃是形上学所析知的生命之理在现实生活之中的实现。
这种以形上本体论为第一义来释儒、注重“形上下贯于道德”的观点,可谓在现代新儒家注重道德心性儒学、注重“由道德而形上”的传统之外对儒学的另一种颇具特色的诠释。具体讲,这种颇重形上学的儒学诠释在儒学传统之中有从《易经》《中庸》至宋明理学一脉相承的传统为根据,在新士林学派之外亦有方东美以及大陆学界的朱伯崑先生约略可为同道。并且,相比于新儒家以德性开出知性的理论架构,罗光此说对“独立的形上学”的注重无疑更易于顺畅地安立知性主体,进而更好地接纳现代科学理性精神,这也正是以罗光为代表的新士林学派所津津乐道的一点。当然,也许新士林哲学家的问题在于如何契接儒家德性精神的本体论根基,因而罗光的儒学诠释亦有不尽完备之处;不过,如果中国哲学史诠释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基于哲学家对历史独具慧眼的默契与领悟而开启现代中国哲学建构的新理路,此举便不无意义。也许新士林哲学家可以提醒我们探讨:儒家在道德心性论的传统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值得“接着讲”的精神传统?甚而,所谓传统儒家之最主流的传统,是否就是建设现代中国哲学所最值得接续的传统?而那些所谓非主流的传统,在现代中国哲学的建构中是否值得接续?如果从现代中国哲学建构的角度着眼,罗光的儒学诠释便不失为一种有意义、有价值的尝试。
第二,形上学与上帝信仰不相违背,且内在包含对最高尊神信仰的要求。就传统儒家思想看,罗光肯定道:“在这种伦理生活中,宗教的成分非常轻……中华民族由具体思想时代进入了抽象思想时代,人性和人心代替了上天的信仰。自孔子开始,一直到清代的儒家,少有人提到上天的信仰。”[2]ⅩⅣ-ⅩⅤ但他认为,这并不代表儒家不讲宗教信仰,而是因为儒家偏重人生之道,在形上学方面未作进一步探求和追问,我们如果进一步追问,便可见其隐含有对信仰的内在要求,因而必须承认儒学是以其源头之处的尊神信仰作为一贯基础的。这种进一步的追问,便由罗光借鉴士林哲学的理论逻辑加以展开。
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士林哲学最重形上学,其核心是对“有”(Ens,英文Being)的探讨。“有”作为世间万有的代表,是人对于外界客体的认识所能有的第一个概念。“有”的构成因素为“在”(存有,Esse)和“性”(即本性或理),阿奎那以“在”为有的先决条件,继此而有其形上学的两个中心观念,即现实与潜能(Actus et potentia):现实是“有”的完成,为现在实在的“有”,也称“行”或“成”;潜能为可能之有,也称为“能”,含义为“不是实有而可以有的”。[8]潜能为隐藏的能,尚未确定,含有各种可能性;现实即是把潜能予以肯定、确断、完成,不再是可能的变动性。阿奎那的形上学以“完成之行”(现实)为最有价值的,这也正是士林哲学的实在论立场,即以“有”为实有,“有”即是“行”和“成”,于是最完满的“有”为最完全的“行”,不含任何潜能,称为“纯净的行”(actus purus)。此纯净的行是“有”的整个实现、整个完成,因此世界上只能有一个纯净的行,也就是基督教所信仰的最高的“绝对实体”——天主。“绝对实体”即是纯净之行,本体完全确定,不会有变化,于是在本体上必为全美全善全真。而宇宙万有,便是由这个最完全和最确定的“第一实体”创造出来的。
以此衡量儒家形上学,则可见儒家是以潜能为重、为先的。罗光在《中国哲学大纲》中指出:“中国哲学的宇宙论跟西洋哲学的宇宙论,一个根本不同之点,就在于宇宙第一实有体的本性。中国儒家所讲的‘太极’,道家所讲的‘道’,都是恍惚不明,本性不定。士林哲学所讲的第一实有体,则本性最完全,最确定。”[9]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形上学谓万物由道或太极的变化而生,道与太极有无限的变化,那么其本体便不是完成而是潜能;而依据士林哲学的理论逻辑,潜能作为未完成的存在是不可能作为世界最终本体的,因而其存在必定还要基于另一完成的最高实体。并且,按照士林传统的理路,任何物体由潜能到现实的变化都必须有一个在其自己之外的动力因,而这也只能是由最完满的天主这一“不动的推动者”(unmoved mover)所赐予的创生力。因而,儒家在讲天地变易之道的同时必须先肯定一个最高实体的存在,落实到儒学传统之中便是《诗》《书》中的超越的帝、天之人格神信仰。
这里以士林哲学形上学的理论逻辑为典范来框衡儒家形上学,大体是用一种外在于儒学传统的本体论进路,推出了“儒学不得不肯定一个超越的上帝信仰”之结论,这便是罗光始终强调的发掘儒家形上学中隐而不显但又不可或缺的第一实体“上帝”的理论任务。也正是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罗光对儒学所未能进一步作出追问的理论逻辑进行了“补全”。应当说,这是罗光以士林哲学的理论为模版来审视儒学而作出的“创造性诠释”,这种对儒学传统而言较为陌生的形上学理路的加入,不能不说有些勉强为之的意味,仅仅凭借儒学在其产生之初的些许“外在超越”的信仰根芽是很难为其找到充分合理的论据支撑的。与此相应,罗光所追求的理论目标——在儒学中为“上帝”的存在确立形上学本体论的根基,也就成了无本之木,难以真正自圆其说。
三、向超越界开放的道德之学——超越儒家哲学
罗光儒学研究的第三个重点在于儒家道德论。他主要致力于探讨儒家道德的人性论基础,进而在儒耶对比的视野下评价儒家的道德境界。
罗光对儒家道德之核心——人性论问题进行了独特阐释。他在将儒学与士林哲学的传统进行对比后指出:“西洋哲学所讨论的人性(Nature),为行为善恶标准,这和中国儒家所讨论的人性在意义上相同;但是理学家所讨论的人性,又有另外一种意义,即是人之所以为人之理,这种意义则和西洋传统形上学所讨论的性相同。”[10]709-710因而,根据罗光的阐述,中国儒学的人性论同时关涉了形上学和伦理学两个领域。罗光主张将道德法则释为人性,只在伦理范围内讨论。因而,他认为先秦人性论更为合理:《中庸》所说的“天命之谓性”继承了《诗》《书》里面由“上天”造生人物并为之制定规则的观念而将人性释为上天规定的行为规则;孟子继承《中庸》的观点,所讲的天仍为《书经》所说的“上天”,人生之道即是秉承这种规则去生活,同时,孟子从另一方面,以性为人心之所同,为人心生来所具有的倾向,讲明此天定法则可以由人心的天然倾向表现出来。进一步地,罗光反对宋明理学把人性问题上溯至本体界的做法,也反对理学以本体的气之清浊为性之善恶根据的观点。他认为,宋明理学不能完满地解决人性问题,因为理学家们混淆了两方面的人性论(形上学和伦理学),也混淆了本体论的善恶和伦理的善恶,“朱熹讨论人性,以人性为存有之理,又为行为的善恶标准,把西洋哲学的两方面人性混在一起。同时……为追求伦理善恶的标准,却又进入形上本体论,追究人性本体的善恶,把西洋的本体之善和伦理的善恶又混合一起”[10]711。可见,罗光依据其所接受的西方士林传统,即严格区分形上学与伦理学、事实与价值并且只承认“形上下贯于伦理”,不能认同宋明理学由道德价值溯至本体领域、谓价值之善即是事实之真、进而在事实界(此儒家事实界本质上就是一个价值世界)寻求本体根据这样的理论特点。在士林传统中,一切学术以形上学为基础,而形上学没有善恶问题,只有“存有”成不成全的问题。尽管其现实之“在”未必成全,但从“性”上讲每一个“存有”都是成全的,因而一切“存有”在本体论上均为善的。这便是罗光所主张的与伦理善恶大不相同的本体之善,而伦理行为的善恶,因其只是反映出对道德法则的符合与否,是不能从本体推求的。
进而,罗光从儒耶对比的视角评价了儒学的道德境界。他讲,儒家精神生命的目标在于“与天地合其德”[3]308,而天地之大德为生生不息,因而圣人的心灵生命超越宇宙万物,参与天地之德,已达到很高的超越境界。但进一步分析起来,天地的生生之德实际是“上天”造物的创造工程,所以儒家的天人合一“不见于人的本体和造物主的本体,而是见于造化的工程,在生生工程上相合”[3]308。也就是说,与儒家形上学的“生生”之“有”对于最终创造实体的“一间未达”相应,儒学在境界上便只成为自我发展的“伦理性超越”,未能契悟终极之本根。儒家境界论应当进一步提升理论层次,进至“本体的超越”境界,达于对最终本体“上天”的信仰。唯有达到“本体超越”,儒学方可真正在学理上契接其历史源头之尊神信仰的超越智慧,亦与基督教士林哲学的义理和信仰实现会通。显然,此处的理路与上文关于形上本体的分析一脉相承,也是以士林哲学、基督信仰作为最终的境界归趋。
综上而言,罗光的儒学研究始终着力于会通儒家与士林哲学。然而,出于一个哲学家的敏锐洞察,他的研究首先立足于对儒学自身特点的分析,因此,其对儒学之信仰源头、儒家形上学和“由形上而伦理”的义理逻辑的分析,均不失为有意义、有启发的理论洞见。不过,士林哲学的学养背景和天主教信仰的人生归趋,使他最终拘于以士林哲学、基督信仰作为唯一真理之理论逻辑,在终极的本体阐释和境界评判中重归于耶。尽管如此,作为20世纪港台地区与现代新儒学并立的学术传统,罗光对儒学的现代阐释展现出一种迥异于新儒学的致思取向,在现代儒学史上具有典型性和独特性,可以为儒学传统的现代重建提供有益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樊志辉.台湾新士林哲学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7.
[2]罗光.中国哲学思想史·先秦篇[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6.
[3]罗光.生命哲学(订定版)[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6.
[4]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9.
[5]罗光.儒家形上学[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6:序言1-2.
[6]罗光.儒家生命哲学[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6:1.
[7]罗光.儒家哲学的体系[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6:192.
[8]罗光.士林哲学·理论篇[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6:853-854.
[9]罗光.中国哲学大纲(下)[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6: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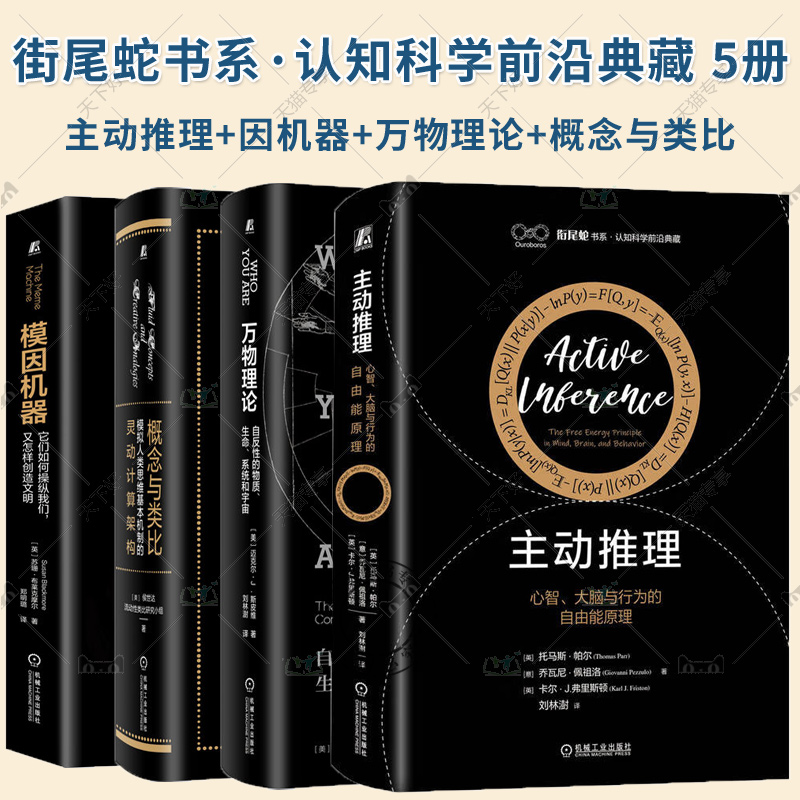
[10]罗光.中国哲学思想史·宋代篇(下)[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6.
[作者简介]吴倩(1983-),女,河北邢台人,副教授,博士,从事中国现代哲学和儒家哲学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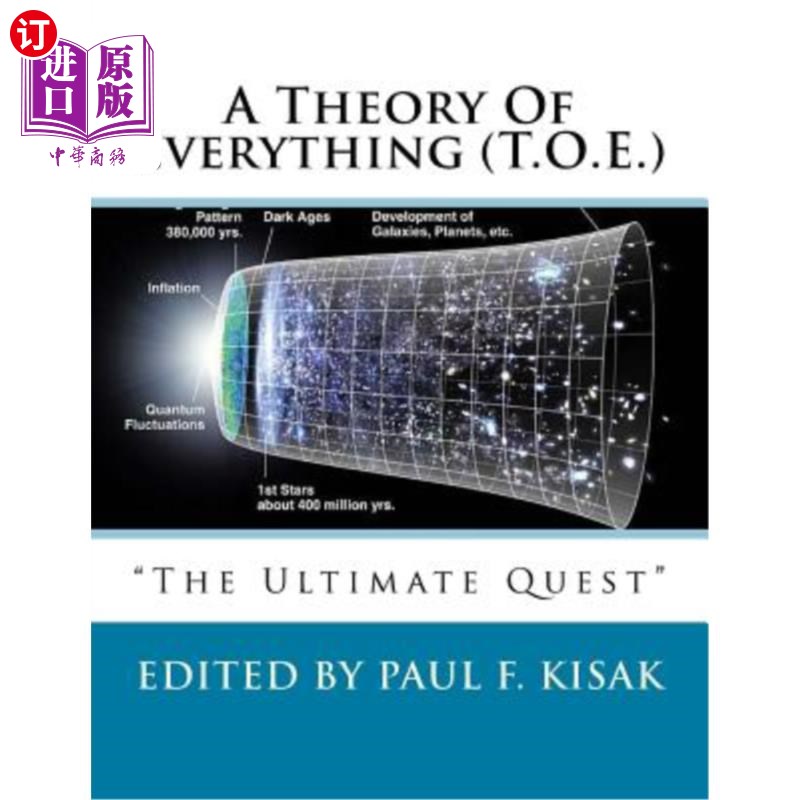
标签: 万物理论

